刘泉开因严重肝炎陷入持续昏迷。
那是1998年7月,身为南昌大学医院的医生,他在昏迷之后经历了一段奇妙旅程。后来,他把这件事写在了论文里。
“我早已无知无觉,冥冥中思绪似乎脱离了肉体,飘浮起来,穿越了阴暗的隧道,前面一片红光。我看见了祖母和父亲,祖母给了我最爱吃的红薯干和炒花生,我欣喜若狂但伸不开手,好似被绳子缚着。我想求救,可叫不出声。
父亲把食品抛洒开去,天空中顷刻间飘下朵朵雪花。祖母和父亲突然不见了,我又满足又遗憾,转身去追赶他们,飘向一个黑暗但不可怕的路口,似乎有什么东西挡住我,把我重新拽回残酷的现实中。我曾经历的与亲人相会的激动、喜悦、宁静的场景,全都消失得无踪无影。”
随着医疗技术的不断发展,很多已经“死了”几分钟甚至几小时的人,被硬生生拉回人世间,从而有机会回答一个问题——
人在临终前一刻,会有怎样的体验?
研究显示,有一部分人可能会经历与刘泉开类似的“濒死体验”。
心跳骤停但抢救回来的病人里,大概十分之一记得自己经历过“濒死体验”。在四个国家的前瞻性研究里,濒死体验发生率平均有17%。
濒死体验是什么
1975年医学博士雷蒙德 · 穆迪(Raymond Moody)在《死后的世界生命不息》一书里创造出“濒死体验”这个词。自那以后,不少科学家开始研究这个领域。
“濒死体验”(Near-death experiences, NDEs),指的是身体在极其虚弱、接近死亡时,会触发一系列反应:痛感消失,感觉自己脱离了身体,向上漂浮,见到逝去的亲友,回顾自己的人生,穿越黑暗隧道,在尽头看到明亮的光,在光里强烈感受到“爱、喜悦、包容和平静”。

隧道尽头看到明亮的光|@snowcat/unsplash
不同人“回来”的方式不同。有的人是瞬间从光里回到病床上,中间没有任何过渡。有的人则是被逝去的亲友告知,自己时间未到,必须回去。
海明威(Ernest Hemingway)年轻时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曾被弹片击中,重伤濒死,他后来写信回家说,“伤后一度面对死亡,感到死非常容易,就像灵魂离开了身体,飘到半空中,然后又返回躯体。一切依旧。”
《柳叶刀》2001年发表的一项荷兰研究询问了344个心脏骤停后成功复苏的病人,其中62人(占比18%)记得经历过典型的濒死体验:有积极的情绪、意识到自己死了、灵魂出窍的体验、穿过隧道、与光交流、看到丰富多彩的颜色、看到星体天河等景象、见到已逝的人、回顾自己的人生、感觉到某种边界的存在。

灵魂出窍的体验|@Louish Pixel/flicker
心理学家肯尼斯·林(Kenneth Ring)调查了盲人的濒死体验后发现,即使是出生时失明的人,描述的濒死体验也有视觉元素,而且与有视力的人描述的濒死体验基本一致。
比如一个5岁的盲女孩玛塔(Marta)在走进湖泊后发生了这样的濒死体验——
“我慢慢地在水中呼吸,失去意识。一位穿着明亮白光的美丽女士把我拉了出来。那位女士看着我的眼睛,问我想要什么。我什么也想不起来,后来才想要环绕着湖走走。当我这样做时,我看到了在“现实”生活中我看不到的细节。只要我想,我可以去任何地方,甚至是树顶。我第一次能够看到树上的叶子、鸟的羽毛、鸟的眼睛、电线杆上的细节以及人们后院里的东西。我的视力远远好于2.0。”
是真实还是编造?
“濒死体验”曾经被视为人们幻想或编造出来的东西,或者是临终前的精神错乱。研究濒死体验多少有点吃力不讨好——对宗教人士来说,这种研究太亵渎神圣了;对科研界来说,这种研究又似乎……不太科学?
大部分没经历过濒死体验的人,都觉得这些体验挺可疑——处在严重创伤甚至心脏停跳状态下的人,怎么能“记住”自己经历过什么呢?
有些濒死体验的确可能是编造的,尤其是那些情节过于曲折丰富的。2010年的畅销书《从天堂回来的男孩》,作者是一对2006年双双发生严重车祸的父子,书里描写了儿子亚历克斯 · 马拉基(Alex Malarkey)在车祸后昏迷的两个月里去了天堂,看到天使带他穿过天堂的大门,见到耶稣,也见到魔鬼,魔鬼有三个脑袋、红色的眼睛、肮脏的牙齿和火焰组成的头发。在2015年,亚历克斯写公开信,承认他的整个天堂之旅都是虚构的。此书也因此被下架。

男孩亚历克斯经历了严重的车祸,虚构了天堂之旅|Tony Dejak/AP
然而,报告有过濒死体验的人数实在太多,许多来自没有宗教信仰的医学专业人士,而且很多体验都有着共同点。
死后的“世界”不一定是真实存在的,但那种“曾经抵达另一个世界”的感觉很可能是真实存在的。
为了尽可能减少记忆错误,目前已经有了十几个关于濒死体验的前瞻性研究。研究人员在医院寻找刚刚经历过医疗紧急状况(比如心脏停跳)的病人,取得病人同意后,问一些开放式的问题,比如“在医生试图抢救你时你经历了什么?”
如果病人的回答里有不同寻常的部分,研究人员再去比对病人的治疗记录,看看有没有什么能对得上的时间点,或者可以解释那些经历的因素。
研究人员着重寻找的是所谓的“非传统感官的真实感知”,比如说,病人看到或者听到了不应该被感知的事物,而且那些事物后来得到了佐证。
当然,这样的案例少之又少。
2001年的《柳叶刀》论文里记载了一个冠心病房护士报告的“病人灵魂出窍”案例。
“夜班时,救护车送来一个面色青紫的44岁男人,他大概一小时前被路人发现昏迷在草地上。入院后,他接受了电击除颤和心脏按压,给他插管时,我发现他嘴里有假牙,于是摘掉了假牙,放在小推车上,同时我们继续给他心肺复苏。一个半小时后,这个男人的心律和血压恢复正常,但仍在昏迷状态,他被转到重症监护室。
过了一个多星期,他才被转回冠心病病房。我负责给他发药,他一看到我就说,“这个护士知道我的假牙在哪,我被送进医院时,你把我的假牙放在推车上了,推车上有很多瓶子,下面还有抽屉”。他能准确而详细地描述他被抢救的那个小房间,以及在场医护的外貌特征。我惊讶不已,因为当时他处于深度昏迷的过程里。我接着追问,他说他记得看到自己躺在床上,旁边医护在抢救他。他拼命试图告诉医护他还活着,拜托一定要继续心肺复苏,但没能传达。的确,当时医护很不看好他的预后,因为他入院时的状况很差。”
这个病人四周后出院了。
2014年,美英研究者发表在《复苏》(Resuscitation)期刊上的一项研究,纳入了15家医院里2060个心脏骤停的病例,其中有101人接受了访谈。
这101人里,46人对抢救过程没有任何记忆,55人则记得一些事情。
一个57岁的男子记得自己有俯视的视角,而且准确地描述了他心肺复苏过程里的人、声音和活动——
“我穿过隧道,向着一道非常强烈、但又不会炫目的光。隧道里还有些我不认识的人。……有个美丽的水晶城市,一条河流穿过市中心,河水清澈透明。许多没有脸的人在河里沐浴……非常动听的歌声,我感动落泪。接下来的记忆是我向上看,一个医生正在做胸外按压。
……
我听到护士说,“444 心脏骤停”,我感到害怕。我从天花板上往下看,看到我的身体和周围一切,医生把什么东西塞进我的喉咙,同时测量我的血压。我看到护士往我的肺里泵气,同时测量我的血气和血糖。
……
(心跳骤停之前)我正在和护士说话,忽然间,我不在了。我肯定是失去意识了。但我清楚记得一个机械语音说“电击病人,电击病人”。
我低头看着我、护士、还有另一个矮胖的男人,他穿着蓝色的手术服,戴着一顶蓝色的帽子,我能看出他是秃头。
我记得的下一件事,就是在床上醒来,感到十分愉快。
第二天,我又见到了那个穿蓝色衣服的人。”
医疗记录显示,这个病人的确被电击过,他认出的那个“蓝衣人”也的确在心跳骤停期间参与抢救。
如果幻觉指的是“不符合客观现实的认知”,那么濒死体验里有些部分应该不属于幻觉。
这个研究还有个非常有意思的设置——科学家们事先在15家医院的急救室里放了一些架子,每个架子顶端贴了张只有从天花板往下看才能看到的图片,图片各不相同,有人物、动物、标识、报纸标题等。如果有病人真的漂浮到天花板上往下看,ta有可能能说出那些图片的内容。
迄今为止,还没有“能描述图片内容”的案例出现。
濒死体验还能“共享”?
最难解释的,还有“共享濒死体验”(shared death experience,SDE)。
在病人临终时旁观的亲友或医护,感觉自己经历了死者从生到死的过渡过程。有人描述房间里充满灿烂的光芒,听到难以形容的美妙音乐,感觉到了死者的“人生回顾”,感知到死者已故亲友的幽灵,甚至看到死者死亡时半透明的“雾”离开死者身体。
“遥感死亡”(Remotely Sensing a Death)也被归入“共享濒死体验”。报告的人在某一刻忽然心有所感,想起了某个人,事后确定那就是那个人的死亡时间。
2021年《美国临终关怀与姑息医学期刊》上的一篇论文收集了164个“共享濒死体验”的案例。
另一个人描述了她丈夫临终时的“共享濒死体验”——
“他的灵魂离开了他的身体,然后他整个站在我的右后方。仿佛我的右侧被激活了一个不同的视角,从那个视角里我看见他,非常活泼,翻着跟头,跑着,叫着,精力充沛。他看起来就像我第一次遇见他时那样年轻,容光焕发,快乐又自由。然后,医院的墙——很难形容,消失了。尽管那时是凌晨两点,但我看见许多灰色的云飘在粉红带橙色的天空中。几乎就像黎明。他的灵魂变成了一团蒸汽,飘进了粉红色的天空中。”
一个美国人报告了自己“遥感死亡”经历——
“我当时正在买衣服,忽然一幅生动的画面浮现在我脑海里,那是我住在英国时的童年好友简(化名)。我忍不住想起我们一起做过的所有事情。她走过来对我说,“我真的很抱歉,但是我必须离开。我做不到了。”我脑中出现了16岁的、自由自在、不再受躯体束缚的简。这时我的电话响了起来。接起来之前我就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我被告知简过世了。”
前阵子,媒体报道的《一对寻亲母子的生死错过》里,其实也有近乎“遥感死亡”的细节——
一对因拐卖失散31年的母子,他们在茫茫人海里寻找彼此多年,曾经联系上,但却没能认出。2022年3月,儿子徐剑锋接到警方电话,告诉他DNA鉴定比对上了,他的母亲是杨素慧。
然而杨素慧已经在2017年因癌症过世。他甚至在凌晨发布的杨素慧过世通告下留过言——
“2017年1月23日清早3点30分,杨茹丹通过杨素慧的朋友圈告诉亲友,妈妈刚刚过世了。8分钟后,徐剑锋在下面留了言:一路走好杨阿姨。他记得当时就像丢失了东西,心里乱乱的。整整5年后,杨剑锋才知道自己是在和妈妈告别。面对多家媒体,他总是提起这天清早的惊醒,提到这种无法解释的偶然。”
到底是什么触发了濒死体验?
还没有一种生理或心理的理论模型,可以解释濒死体验的所有特征。
医生们遇到濒死的人也肯定得先抢救,不可能“抓紧机会”用垂危者们做实验。
现在知道的是,在濒死之前,大脑的确会有高强度的某种“活动”。
2022年刚发表在《老化神经科学前沿》(Frontiers in Aging Neuroscience)的一项研究认为,垂死的人眼前可能会闪回人生片段。
2016年,一个87岁的男子因脑出血被送到医院急救,脑部手术三天后,这位男子又出现了癫痫。为了确定癫痫发作的根源,这位病人被持续监测脑电图,就在这个过程中,男子心脏骤停死亡。
因为这些机缘巧合,他临终前的脑电图被记录下来,就在他心脏彻底停跳的前后几分钟里,他的脑电波里伽马振荡的部分剧增,这种神经元震荡模式通常在人回忆、闪回、做梦、冥想时出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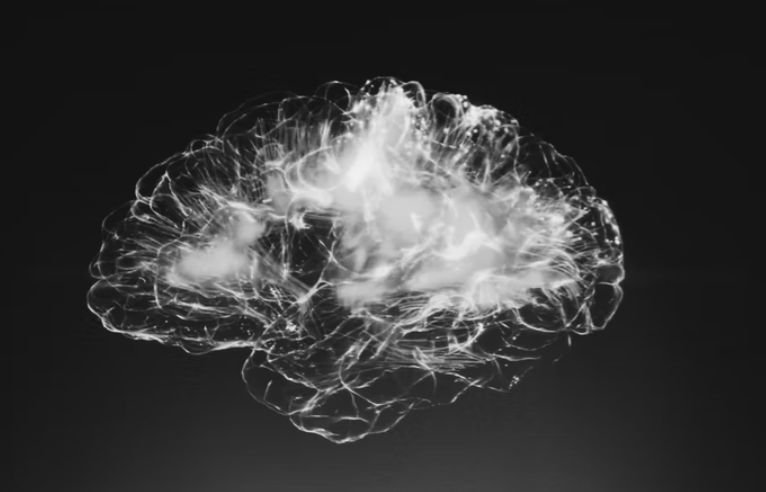
此病人濒死时,脑电波伽马震荡部分剧增|@alinnnaaaa/unsplash
这样的现象在其他动物身上也记录到过,2013年《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刊》(PNAS)上的一篇论文就发现,大鼠在心脏骤停后的30秒内,大脑同样出现了比清醒状态下更强的伽马震荡。
但到底哪些因素会触发濒死体验?过程里又发生了什么?
简言之,不知道。
科学家们认为可能引起濒死体验的因素包括:缺氧、高碳酸血症、内啡肽等内源性神经化学物质的影响、颞叶兴奋、快速眼动入侵、人格障碍、催眠和易受暗示性、人格解体等等……
当一个现象有许多解释时,其实意味着我们对这个现象还没有特别好的解释。
从年轻到年老,任何年龄段的人都可能发生濒死体验。对濒死体验者的研究还显示,他们基本上都是心理健康的个体,在性别、种族、智力、焦虑等特质上都和对照组没有差异。
2001年的《柳叶刀》研究就未能找到引起濒死体验的具体因素——这344个人都经历了短暂的“临床死亡”,大脑经历的缺氧状况类似,用药也类似,心理状态也没有人特别恐惧。
但有人有濒死体验,有人却没有。
对濒死体验最常见的疑问是,濒死时感受到的“灵魂出窍”和“明亮之光”,会不会是因为我们深受宗教影响而想象出的?
不过,在经历濒死体验的几率上,没有发现虔诚的信徒与世俗的无神论者之间有任何区别。那些事先对濒死体验一无所知的人描述的经历,和那些本来就听说过濒死体验的人的经历基本相同。就连对死亡还不太有预设观念的年幼儿童,报告的濒死体验依然有着相同的特征。
也许不是“宗教影响了濒死体验”,而是“濒死体验流传下来,成为了宗教”?
英国心理学家苏珊·布莱克莫尔(Susan Blackmore)年轻时也经历过濒死时的“灵魂出窍”体验,她认为,濒死体验是临近死亡的大脑在压力下过度活跃的产物,有意思的是,濒死体验往往遵循某些特定的顺序,比如一定是先穿越黑暗隧道,再看到白光。她猜测,这与神经递质的级联有关。
另一种猜测是,大脑缺氧、某些治疗药物或是大脑的器质性功能障碍引起了濒死体验,本质上是一种幻觉。
不过,濒死体验似乎能被多种情况触发。手术、分娩、意外事故、心脏骤停、失血重伤、窒息缺氧、还有真正的死亡,都可能带来“濒死体验”。
有时候,并没有“缺氧”,但濒死体验却发生了。甚至还有对濒死者的研究显示,他们体内的氧含量并不低,倒是二氧化碳水平有时候低于正常水平。
另外,也有人提出濒死体验与幻觉不太相同。
幻觉通常是感觉皮质过度活跃而产生的,而濒死的人大脑功能常常是受损状态,这不利于产生幻觉。
真正的缺氧、药物、大脑器质性功能障碍引起的常常是令人恐惧的幻觉,导致患者激动易怒,这与“濒死体验”带来的宁静抚慰是相反的。
还有研究者提出,“经过黑暗隧道、进入到明亮的光和另一个世界里”,会不会是来自一个人出生的记忆。

经过黑暗隧道、进入到明亮的光和另一个世界里 | Javier Esteban/unsplash
然而,新生儿的视觉其实并不好,三岁之前的记忆也很难保留。另外,经由剖宫产出生的人,和经由顺产出生的人,有着同样普遍的“隧道体验”。
还有一种假说认为,濒死体验是梦境的一种。
然而,梦境大多发生在快速眼动期(REM),而抑制了REM的全身麻醉却可能触发濒死体验。
经历过濒死体验的人还往往坚持,濒死体验是他们经历过“最真实”的事情,“比我曾经经历过的任何事都更真实”,“濒死体验绝不是梦,和做梦时的感觉截然不同”。
2010年一项对613名濒死体验者的调查发现,96% 的人认为他们的濒死体验是“绝对真实的”,没有一个人认为它是“绝对不真实的”。
2017年,弗吉尼亚大学研究者发表在《意识与认知》(Consciousness and Cognition)期刊上的一篇论文访谈了122个有过濒死体验的人,发现从记忆的“真实度”来说,濒死体验的记忆 >“ 那段时间发生的真实事件”的记忆 >“那段时间想象出的事件”的记忆。
“真实事件”包括孩子出生;家庭成员死亡;人际关系终结;飓风、野火或洪水等自然灾害;重大手术、疾病等等。“想象事件”包括当时曾经预期的离婚或结婚、工作机会或晋升,担忧过但没发生的自然灾害等等。
被濒死体验改变的人生
濒死体验对于一个人的冲击十分巨大。
按特定顺序发展的濒死体验,其实有点类似“英雄旅程”。
“英雄旅程”是美国文学教授约瑟夫·坎贝尔(Joseph Campbell)提出的叙事原型:一个人因为某些干扰,而离开了原本的生活方式,踏上冒险的旅途,他开始时常常不情不愿,但最终还是克服了重重磨难,在一个决定性的危机里获得胜利,带着战利品以及内在的转变,回归到原来的世界。
从神话传说、荷马史诗、名著小说,到如今的许多好莱坞大片,都有着“英雄旅程”的框架。著名的《星球大战》系列就深受“英雄旅程”的影响。

古希腊时根据荷马史诗所绘的图,图中为海伦和普里阿摩斯|Bibi Saint-Pol/wikipedia
这就是为什么濒死体验拥有如此强大的力量。那些“跨越界限,再回到人间”的人,都会被震撼,被改变。濒死体验像是一剂超强的成长催化剂,迫使人们重新思考自己的人生——当你曾经“死”过一次,你会想以不同的方式再活一次。
很多人说,濒死体验使他们相信来世存在,于是不再害怕死亡。有些人说,自己从前在生活里追求的权力、财富、名望都显得不再重要,他们相信,生活里最重要的是学会如何去爱。他们决心更投入地去爱其他人,去建立联结。
经历过濒死体验的人往往更关心别人,而变得不那么专注工作,也不那么物质主义。有研究者追踪了有过濒死体验的人8年,发现这种转变可持续多年,甚至会越来越明显。
2001年的《柳叶刀》研究发现,在复苏30天内,有濒死体验的人的死亡率明显更高。在几年后,有过濒死体验的人更不害怕死亡,更相信来世。
国内的研究也得出了类似结论。
华中科技大学的吴疆总结了2009~2011年间,武汉两所三甲医院里发生的16例濒死体验,总结出这样的共同点:①躯体上有疼痛或不适感,②心理没有恐惧和害怕,反而有轻松、安详感,③有意识离体、与亲友欢聚、创伤性回忆等超常或超然体验。
吴疆的研究里也发现,“濒死体验”会给人带来自我认识、人际关系、生活态度、生死观念这四个方向的变化。经历过濒死体验的人,更理解和爱护自己,更同情他人,更关心家庭,对生活更加珍惜、热爱、感激,更主动采纳健康的生活方式,同时更泰然地看待死亡。

有过濒死体验的人会更珍惜生活,关心他人,并采取健康的生活方式,看淡死亡|@livvie_bruce/unsplash
不那么愉快的濒死体验
经历过濒死体验的人,通常觉得那是积极甚至美好的经历。不过,也有少数人的濒死体验不那么愉快。
弗吉尼亚大学的精神病学研究者南希 · 埃文斯 · 布什(Nancy Evans Bush)和布鲁斯·格雷森(Bruce Greyson)则报告了三类不愉快的濒死体验:
相反的濒死体验(inverse distressing NDE)
别的体验者觉得愉快的部分,某些濒死体验者觉得糟糕或恐惧。
有人从马上摔下来后感觉自己在树顶上飘着,看着底下的急救人员抢救他的身体,他被吓坏了,尖叫“不!不!这是不对的!放我回去!”但没人听到他的叫声。
有人在分娩中感觉自己灵魂离开身体,飞入太空,一个耀眼的光球向她冲过来,越来越大,越来越靠近她,并最终吞没了她,这使得她非常害怕。
有人因中暑而昏迷,并看到了自己的人生回顾跑马灯,“我被悲伤充满了,经历了许多抑郁。”
虚无的濒死体验(Void distressing NDE)
某些人体验到了巨大甚至毁灭性的孤独。
一个女性在分娩时感觉到自己漂浮在水面上,但在某一刻,平静感消失了,她感觉到孤独,空虚的空间,浩瀚的宇宙,除了她只有一个光球。
一个企图自杀的女性感觉自己被吸入了空虚中,“我被吸入了这个黑暗的深渊或者空虚,我很害怕,我期待着长眠和被遗忘,但这个力量把我拉到了我不想去的地方。”
一个被人袭击的男人感觉自己飘出了身体,“我突然被完全的黑暗包围,漂浮在除了黑暗什么也没有的空间里,没有上,下,左,右。我只能在这个糟糕的境况里反思。”
地狱般的濒死体验(Hellish distressing NDE)
这是最罕见的痛苦的濒死体验。
一个心脏衰竭的人感觉自己掉到了地球深处,那里有一个高大的、生锈的大门,他认为那是地狱之门,惊慌失措。
一个无神论的大学教授,因肠道破裂体验到遇到一群恶毒的生物,被它们抓住甚至撕裂。
一个大出血的女性的濒死体验里涉及到一些“可怕的生物,用灰色胶状的附肢抓我”,41年后她依然记得那些生物发出的呻吟声以及难以形容的恶臭。她的濒死体验里没有神圣的光,没有人生跑马灯,也没有任何美丽或愉快的东西。
人们处理糟糕的濒死体验,大概有三种方法——
①说服自己这是“转变的机遇”。
人们相信自己过去的人生里犯了错,但被给予第二次机会,回到人间改过自新。
②把这件事当成没有发生,或者说服自己那只是幻觉。
有些人认为那就是没有意义的幻觉,不值得为之焦虑不安。
③被持续困扰。不断挣扎思考,为什么会发生这种事?我做了什么?
有些人去做心理治疗。有些人完全闭口不谈,但依然常常闪回当时的景象。
尾声
我们之所以无法理解濒死体验,也许是因为,我们依然对“意识”知之甚少。
人死之后,原本的“意识”去哪里了呢?对唯物论者来说,意识是大脑“涌现”出来的一种属性,我们神经系统里的所有物理、化学、生理过程以某种方式“编织”而成。一旦这些过程被拆散,意识也就不复存在。就像你关掉投影仪,曾经投出的图像并没有“去哪里”,它就是简简单单地不存在了。
但这种“编织”“涌现”到底是如何发生的?一个严重受损的濒死大脑,为什么能回光返照,编织出“超级真实”的体验?
也许这些谜团解开之日,就是我们理解意识本质之时。
当大脑缺血缺氧时,人的大脑就像一座正在经历停电的城市,灯火一块块地熄灭。

人类不断在探寻意识的本质|《黑客帝国》剧照
不过,当大脑大规模的电活动终止时,有些零散的神经元可能依然在产生一些电活动,维持着“自我”的存在感,并根据过往的经历碎片,创造出濒死体验。
也许,“人为诱导濒死体验”会是一个研究方向。
已经有实验成功在健康人身上诱导出了濒死体验。接受测试的是一些美国飞行员,当他们经历大概五倍重力加速度时,飞行员因为大脑缺血而晕迷,此时撤去额外的重力加速度,10~20秒后,飞行员恢复意识,并逐渐回忆起之前的感觉——隧道般的狭隘视野,明亮的光,平静的漂浮感,愉悦甚至欣快感,以及短暂但令人激动的梦境,梦境里常常有家人出现。
另外,有研究者认为,致幻药物LSD也经常诱导出和濒死体验类似的感觉:人生回顾、灵魂出窍、与温暖美丽的光合二为一,体验到强烈的幸福感和意义感。
既不必把濒死体验看成“绝对真实的灵性体验”,也不必把濒死体验看成“无关紧要的谎言与幻觉”。濒死体验可以是改变人生的重要经历,也可以帮我们更理解生命和死亡。
对濒死体验的探究,也是对人类本质的探究。
身为人类,我们总是在探索世界,探索内心,努力理解自己,也理解万事万物的运作方式。我们观察、思考、提出假设并做实验测试,我们精心选择词语来描述我们发现的东西,我们从时间长河里捞出无数碎片,组合提炼出完整的人生故事,给一切赋予解释和意义。
对“濒死体验”的研究,并不意味着一定有“死后世界”的存在。它更多地意味着,当我们不能再治愈,不能再挽留时,我们依然可以去安慰,去帮助。
如果濒死体验大部分是温暖的、平静的,那么知道了这一点的我们,在走向死亡时,也会更加坦然无惧。
正如海涅所说:“死亡是一个凉爽的夜晚。”有时候,温和地走入良夜,也是一种选择。

《星际穿越》中,太空基地库珀站上的石碑刻着英国诗人狄兰·托马斯的诗歌《不要温和地走进那个良夜》|《星际穿越》剧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