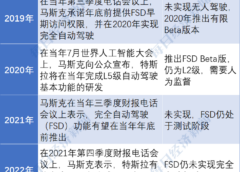两会来临,《中国经营报》记者就中国经济发展趋势,金融体制改革等相关问题,对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院长、国家发展研究院名誉院长林毅夫进行专访。

林毅夫 全国政协委员 广州粤港澳大湾区研究院理事
林毅夫认为,2019年到2035年,我国仍还有8%的增长潜力,目前来看,产业结构升级、新经济发展、新能源、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均存在较大的投资和增长空间,要对中国经济有信心。
谈到金融体系改革,林毅夫建议金融结构方面,应进一步推进中小银行发展,对中小银行匹配更为合适的监管规则;金融价格方面,应逐步放开储蓄利率限制。同时,谈及地方金融业发展,林毅夫表示,各地不应盲目追求金融业的绝对发展,应以实体经济的金融需求为准,否则容易造成金融抑制或者金融泡沫,适得其反。
针对地方隐性债务问题,林毅夫建议修改财政制度,允许地方政府在一定条件下可有赤字财政,缓解期限错配问题。
《中国经营报》:2022年开端,你推出两本著作——《中国经济的前景》、《论中国经济的发展》,你认为,中国经济从2020年到2035年仍然还有8%的增长潜力。新时期,中国经济的引擎在哪儿?
林毅夫:今年我的提案主要围绕“稳增长”。我个人认为,中国经济发展仍有较大潜力,要对中国经济有信心。首先,我国传统产业方面有较大的追赶空间。如果参加全世界最大的法兰克福工业展,就会看到我国传统产业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差距意味着存在产业升级、技术创新空间。
面临产业升级,我国仍具有较大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的空间,相对成本较低。可以看到,发达国家长期以来的经济平均增长速度一般在3%-3.5%之间,但我国改革开放后,经济连续40多年实现超过9%的增长,重要原因之一就是我国合理利用“后来者优势”,即利用和发达国家的产业技术的差距,作为技术创新、产业升级来源。
其次,我国在新经济方面也具有较大的发展潜力。从独角兽数量看,2019年全世界494家独角兽企业,其中,中国206家,美国203家;2020年全球586多家独角兽企业,其中,中国227家,美国233家,两国不相上下。新经济有很多创新空间,中国具有世界最大的市场,数字产业化具备优势。
目前,我国正在逐步发展5G通信,建设相关基站。可以看到,过去4G网络的发展建设,创造了大量新机会。而5G通信的落地,亦将是新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
最后,基础设施方面我国仍有发展空间。当经济周期下滑,政府财政政策支持投资,而基础设施、环境等领域均是重要的投资方向。
《中国经营报》:“西天取经解释不了中国的新经济现象”,你认为,相对发达国家,我国目前更合适的金融安排是地区性的中小银行。近几年,中小银行一定程度上出现合并潮,在你看来,我国中小行如何实现科学发展?
林毅夫:金融应服务实体经济,这是其核心功能。而从实体经济特性看,我国绝大多数生产活动来自农业,以及微型、中小型制造业和服务业,从数据来看,我国中小微企业贡献了约50%的政府税收、60%的GDP,还有更多的就业和创新。但实际上,它们大多数不能得到大型银行、股票市场、风险资本的良好服务。匹配来看,更适合的金融安排是地区性中小银行。
长期来看,从根本上缓解中小企业的融资约束,关键在于改善银行业结构,满足中小企业对中小银行的金融需求,发挥中小银行善于甄别企业家经营能力的比较优势,而不是通过行政干预要求大银行服务于中小企业,这是新结构金融学关于最适宜银行业结构的基本理论和政策主张。
推动中小银行进一步发展,监管体系要跟上。目前,我国按照针对大银行的《巴塞尔协定III》来进行监管,《巴塞尔协定III》主要适用于发达国家的金融制度安排,而我国作为发展中国家,必须意识到中小银行的规模特征、风险特征与大型银行均不同,两个群体应区别监管,中小银行的发展需要全新的监管规则、流程创新。
《中国经营报》:目前为止,我国金融体系基本仍是双轨制,尚未完成从双轨向市场并轨。你认为,下一步,金融体系改革的关键点是什么?
林毅夫:目前,金融体系改革有两个重点:一是金融结构改革,二是金融价格改革。
首先,我国目前的金融系统以大银行和股票市场为核心,地区性中小银行的数量分布上不足。究其原因,这种安排其实是双轨制改革所遗留的历史产物。改革开放初期约80%的实体经济都是国有企业,其中又以大型国企为主,它们大多违反比较优势,缺乏自生能力,需要依靠着政府补贴。
改革开放恢复金融体系时,我国设立了以大银行为主的金融体系,通过压低资金价格来满足大型国企的需要。20世纪90年代,国家逐渐开放股票市场,主要目的仍旧是帮助大型国企脱困。至此,我国就逐步确立了以大银行和大股票市场为主的金融体系。虽此后历经几番改革,但未改变根本格局。
金融结构基本上是偏向于服务大企业,但是我国实际上有大量农户,微型、中小型企业的金融需求存在,金融结构需向后者倾斜,重点发展中小银行。
金融价格方面,我国早期金融改革,为扶持大型国有企业,将贷款利率、储蓄利率压低,近年来贷款利率逐步放开,实现市场化,但储蓄利率并未提高。一般西方发达国家的存贷款利息差最多是一个百分点,但在我国可以达到三个百分点甚至更高,二者不对等、不平衡。
下一步,我们应该放开储蓄利率的限制,让资金所有者得到应有的回报,这同样有益于收入分配优化,是金融改革重点。
另外,对于战略型产业的补贴,要更多运用财政而不是银行的低价贷款,改革就是要使银行贷款价格回归一般市场水平。
《中国经营报》:近些年,我国结构性去杠杆取得明显效果,2021 年末我国非金融企业部门杠杆率为 153.7%,比上年末低 8.0 个百分点。你认为,我国非金融企业杠杆率未来走势是怎样的?
林毅夫:长期看,杠杆率下降是趋势。随着经济发展,企业规模越大,为其提供金融服务的主体将逐步从银行机构转向股票市场。因为当产业结构还不处于世界前沿时,企业所用的技术、所生产的产品、所销售的市场均较为成熟稳定,如果行业符合比较优势则其景气度较高、增长前景稳定、资本投资回报率较高,此时产业中的企业会倾向于通过举债的形式加杠杆。
随着产业结构升级,向世界前沿转型,企业所使用的技术、所生产的产品、所销售的市场都面临较高的不确定性,风险也随之增加,此时产业中的企业会倾向于采取股权融资的方式以分散风险和降低利息费用,杠杆率亦随之下降。
当然,经济会周期性波动,当经济下行时,需要货币政策支撑,大部分资金仍需通过银行发放,流入企业及家庭单位,促使杠杆率抬高,但这是正常现象,当我国经济恢复步入宽松期,企业利润提高后偿还负债,杠杆率自然会降低。
《中国经营报》:你认为地方政府隐性债问题应如何化解?
林毅夫:可以说,地方政府隐性债务是中国特色。因为按原有规定,我国地方政府不能有财政赤字,但推行逆周期财政政策时,实际主要是由地方政府经投资平台举债来实现,这就造成地方隐性债务杠杆率升高。
但是,我国总债务率并不高,即使将地方投资平台债务全部计入,我国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债务占GDP的比重,与其他国家相比仍不算高,更何况我国地方政府负债绝大多数用来投资基础设施等,形成回报的资产,净债务更低。
实际上,地方投资平台最大的问题是短债长投,基础设施建设时间长,而银行借款主要是短期贷款,导致期限不配套,解决这个问题,应给予制度配套。
前几年,我国进行改革,允许中央政府代替地方政府发债,不计入地方政府负债,规避了地方政府不能财政赤字的问题。但从长期看,我认为应修改财政制度,允许地方政府在一定条件下可以有赤字财政,改善中国地方政府的发债机制,为其提供长期资金来源,缓解期限错配的问题,只要经过合法程序即可。
《中国经营报》:近期各地区金融业“十四五”规划陆续出炉,金融业成为地方经济发展较热门的选择,资本市场能够推动实体发展,但亦可能会产生金融泡沫,地方政府对此应如何判断?
林毅夫:整体上看,随着经济发展,我国金融发展水平也会不断得到提高。然而,一些处于类似发展阶段的省市的金融发展差异依然很大。另外,一些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较低的省市,金融发展水平或相对更高。这一方面反映出一些地方金融相对滞后,另一方面也反映出一些地区金融过度发展。
金融虽然是盈利性强的赛道,但并不是所有地区都适合重点发展,金融业规模经济大,相对集中,不能够遍地开花。如果在不具备相应条件的地区过度发展金融业,大概率只会短期带来虚假的经济繁荣,长期来看注定产生风险并失败。
因此,各地不应该追求金融业的绝对发展,应以实体经济的金融需求为准,否则容易造成金融抑制或者金融泡沫。各地最适宜的金融结构安排,必须与特定发展阶段的要素禀赋结构及其内生决定的产业结构相适应。可以采取新结构金融学的基本思路,以及五类产业因势利导的操作方式来因地制宜地落实国家制定的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发展的大政方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