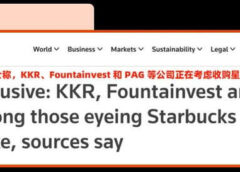作者 | 郑永年
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
来源 | 《贸易与理性》(郑永年教授新作)
导读:为什么中美两国经贸依存度如此之高,美国却宁可承受巨大经济损失,也要对抗、打压中国?郑永年认为:两国的经贸交往越深,冲突越易发生,负面影响也越大,例如一战就是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发生的。因为经济全球化在带来好处的同时,也造成了从一国内部到各国之间的收入差异和分化,这为冲突埋下了种子,使得经济因素向战争转化。更令人担忧的是,充斥于当今世界的各种“认同政治”已变得毫无底线,如此下去,社会内部的冲突甚至内战,正如国家战争那样,也可能变得不可避免。
为何经贸相互依存也可能会导向战争
作为世界上最大的两个经济体,中美关系不仅仅是单纯的两大国关系,更会影响到很多其他国家。这些国家和中美两大国都有着复杂而深厚的关系,在中美关系平稳的时候,它们都可以从两边获得利益,但一旦两大国关系恶化,它们都会受到深度影响。
一些国家可能在短期内可以获取一些利益(例如,从中国退出的产业和资本进入这些国家),但从长远来看,这些国家也避免不了中美地缘政治竞争所带来的负面冲击。
中美贸易摩擦能够产生如此广泛而负面的经济影响,这使得很多人很不了解中美两国所进行的贸易战。贸易战显然不是一场双赢游戏,而是两败俱伤,即人们所说的损人不利己,“损人一千,自损八百”;不仅如此,贸易战还波及很多其他国家,甚至是美国的盟友。
更为重要的是,今天人们把中美之间的经济冲突界定为“贸易战”或者“经济战”,就表明这已经大大超越了传统“经济竞争”的范畴,而进入“战争”状态。
传统上,人们一般认为经济竞争不可避免,并且经济竞争并非零和游戏,但战争则往往是零和游戏。这又使得很多人担心,今天中美之间的贸易战如果不断升级,是否会导向另一类战争,无论是热战还是冷战。
这种担忧不仅合理,而且也是必要的。人们可以把两国之间的经贸关系,视为经济区域化和全球化的结果。两个互不交往的国家不会发展出任何经济关联,也无所谓贸易冲突。
两国之间的经贸交往越深,冲突就越容易发生,负面影响也越大。历史地看,经济的区域化和全球化的确给参与国家带来巨大的好处,但也不断地导向冲突甚至战争。
这些年来,人们总是把今天的状况,比喻成为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情形。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世界经济经历了前所未有的经济区域化和全球化,经贸的频繁往来和经济上的互相依赖,不仅发生在欧洲国家之间,而且也发生在欧洲国家和其他区域国家之间。
但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就是在这样一种情形下发生的。事后诸葛亮不少,但事先没有人认为战争会这么快就在这些经济上互相依赖的国家之间发生。

经济竞争导向零和游戏的战争
的确,如果仅仅从经济的角度来看,很难理解为什么非零和游戏的经济竞争,会导向零和游戏的战争。但如果从更深层次的政治经济关系来看,不难发现,冲突和战争也是国家之间的常态,正如它们之间的经济贸易一样。任何形式的战争都是要付出巨大的代价的,大的战争往往招致无数的生命和财产的损失。但人类为什么还要战争呢?
德国社会和政治学家奥本海默(Franz Oppenheimer)在论述国家的起源时,总结出了两种方法,即经济方法和政治方法,前者通过人们都可以接受的“交易”方法,或者“契约”方法,而后者则倚重“权力”和“力量”。
奥本海默本人则倾向于政治方法,因为经验地看,从人类开始产生以来,政治就从来没有离开过,从原始部落到近代国家,暴力是国家起源和发展的永恒来源。
近代商业资本主义尤其是工业化开始之后,人们对战争的根源和如何避免战争有了全然不同的看法。其中,英国哲学家亚当·斯密(Adam Smith)著《国富论》(The Wealth of Nations),为国家的发展寻找到了最有效的经济方法。
斯密认为,国家通过“劳动分工”和贸易就可以致富和积累财富,而无须通过战争和掠夺。斯密之后,李嘉图(David Ricardo)则进一步发展出“比较优势理论”来论证经济方法的有效性。
不过,并不是所有人都认同斯密和李嘉图的观点。马克思最为典型,他认为近代以来的战争,无论是内战还是国家间的战争,简单说就是资本主义扩张的自然结果。
在一个社会内部,资本主义造就了阶级分化,导致了阶级之间的利益冲突,极端一些就是内战;在国际层面,资本主义导致了国家间的利益冲突,极端一些就是战争。
经济因素可以遏制和避免战争这一观点,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和传播。
用经济史学家熊彼特的话来说,如果近代以来民族主义是战争的根源,可以预期,民族主义只是人类远古野蛮兽性的一种遗留物,终究会消失。经验地看,这主要是出于两个原因。

第一是人们看到战争的残忍性和经济上的毫无理性。战争没有赢家,人人都是输家。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给欧洲各国的经济带来了毁灭性的影响。
第二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开始的经济整合。经济整合从欧洲“共同市场”概念开始,扩展到其他各个地区。西方各国市场的整合及其西方市场向其他非西方国家市场的延伸,有效地把有关国家连接在一起,促成了经济的发展。
尤其重要的是,20世纪80年代由美国总统里根和英国首相撒切尔新自由主义革命所引发的新一波全球化,更是在很短时间里把一个广袤的世界演变成为一个“全球村”。国家间经济上的高度互相依赖所能产生的正面效应,反映在了国际关系领域的“互相依存理论”上。
“互相依存理论”加上源自近代德国哲学家康德的“民主国家之间无战争”理论,成为近年来西方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主流。人们深信,国家间经济上的高度依赖,加上政治上的民主化,战争就可以远离人类,实现康德的“永久和平”理想状态。
这种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也基本上决定了美国处理和其他国家关系的态度和方法。那就是,美国必须通过经济方法(开放、市场准入、整合等),促成那些和美国具有经济关系的国家的政治体制的民主化。
也就是说,对非西方国家来说,和美国(西方)国家发展经济关系是有政治前提的。也很显然,这个政治前提充分反映在美国(西方)国家的贸易、投资、国际援助等方面。

国家之间关系冲突的本质
不过,自由主义理论(无论是经济学家还是政治学家)更多地反映了信仰者对世界的一种理想,而非对现实的反映。对西方的现实主义者来说,经济互相依赖的确导致了国家之间的利益相关性,增加了处理国家之间关系的难度,但绝对没有改变国家之间关系的冲突本质。自由主义过度夸大了经济全球化所带来的好处,但大大低估或者忽视了经济全球化固有的负面影响。
历史地看,经济全球化必然造成两个结果:第一,一个社会内部的收入差异和分化;第二,国家之间的收入差异与分化。
在一些国家,内部收入差异和社会分化,经常导致不同社会阶级间的经济冲突,甚至演变成内战;在另一些国家,内部冲突外化成为国家间的冲突,即战争。当多个国家同时卷入时,就演变成为世界大战。
经济关乎利益,利益分配不公就会导致战争,无论是内战还是国家间的战争。就是说,经济因素的确可以导致战争。
但如果人们仅仅从经济因素来理解战争,那还是过于简单。在大多数场合,政治因素甚至远较经济因素重要,人们既为利益(经济)而战,也为荣誉和恐惧而战,而荣誉和恐惧更多的是关乎政治。
实际上,一旦涉及战争,政治逻辑就占据主导地位。近代普鲁士军事战略家克劳塞维茨(Carl Von Clausewitz)说过,“战争是政治通过另一种手段的延续”,无疑揭示了战争的“政治”本质。
克劳塞维茨所说的几乎是永恒的。多少年来,人们一直企图超越经济因素而去寻找战争的根源。人们诅咒战争,祈求战争不再发生,但同时人们也在赞美战争。
人的本性中存在一种倾向,把自己道德化,把他者妖魔化。即使是侵略,侵略者也总能找到战争的“正当性”和“正义性”,并为此而歌颂战争。从古希腊各城邦之间的战争到中世纪十字军东征,战争总是成为人们讴歌的对象。
到了近代,战争具有了更高的道德性。法国大革命以后,基于主权国家理论之上的“民族主义”大旗,引导着人类进入毫无止境的战争。各种论证和颂扬战争的理论一一出炉。
这尤其表现在近代浪漫主义和社会达尔文主义者那里。近代浪漫主义始于英国文学,当传播到德国时进入了政治哲学领域,歌颂战争和暴力,为了国家利益(无论是统一还是发展),一切在所不惜。在社会达尔文主义那里,战争不仅是“适者生存”的必然产物,也是检验人类品质的最高标准。
尽管达尔文本人的“进化论”并没有明显的道德和进步观念,但到了社会达尔文主义者那里,“进化”变成了“进步”和“文明”。所以,战争不仅仅是“适者生存”的手段,更是成为人类进化、“文明”淘汰“野蛮”、“进步”取代“落后”、优胜劣汰的工具。

整个帝国主义时代,人们深信“战争的胜负是衡量一个国家的优劣”的有效手段,列强之间为战争乐此不疲。英国思想家萧伯纳(George Bernard Shaw)曾经说,人类大多都在投资于死亡而非生活,即人们把最多的投资用于战争武器,而非改善人民生活。
这种情况到现在发生了多大的变化?在很大程度上,现在的确是一个全然不同的时代了。如上所说,经济的全球化使得各国互相依赖,“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这在客观上大大增加了战争的难度和成本。
同时,在话语方面,没有多少人公然宣扬战争了。不过,如果足够现实,人们也不难发现,这可能仅仅是表象,人类的本性依然没有发生变化。
和从前的全球化一样,这一波全球化依然产生着同样的问题,即社会内部的不平等和国家间的不平等,而极度的不平等随时可以导向内外部的冲突。从话语来说,人们只是用一种更为巧妙的方式把“优胜劣汰”的观念表达出来而已,包括“文明冲突论”和“民主价值同盟论”等。
再者,和人类的其他很多行为一样,自古至今,战争已经高度机构化和制度化了。对参与战争的主权国家来说,战争有开始的仪式,也有结束的仪式,战争过程更是充满各种仪式。战争因为主权国家而高度制度化,也因为主权国家而被“道德化”和“正义化”。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除了被彻底打败的德国对战争有反思之外,没有任何一国对战争有真正意义上的反思。战败国如日本从未反思战争,而战胜国则依然为“战胜”沾沾自喜。
主权国家或者政府是战争的主体,但推动政府发动或者参与战争的,则是政府背后的各种利益集团。资本可以成为战争的根源,因为资本需要借助政府来打开其他国家的大门,开拓世界市场,掠夺他国的资源,保护他们的海外利益。
但在更多的场合,其他利益集团甚至较之资本更可以直接从战争中获取巨大的利益。例如,美国安全和军工系统在战争中的巨大作用,以至于很多美国人相信战争就是这个利益集团追求自身利益的工具。很难想象,如果没有战争或者战争的威胁,美国如何维持一个如此庞大的战争机器。
更令人担忧的是全球化条件下极端“认同政治”的崛起。今天的“政治认同”已经变得毫无底线。
不仅现存的不同民族、种族、宗教、文明、国家之间的认同差异在迅速扩大,甚至在这些单元的内部也在继续分化,人为地把同一个民族、种族、宗教、文明、国家分化成为不同的民族、种族、宗教、文明、国家。包括民族、国家、文明在内的所有“认同”都是可以人为制造的。如此下去,一个社会内部的冲突甚至内战,正如国家间的战争那样,正在变得不可避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