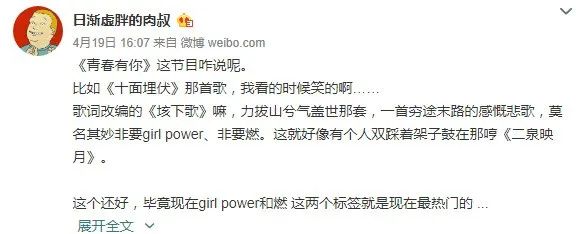《青春有你2》的歌词改编,肉叔之前有发微博吐槽过。 为突出小姐姐们的“girl power”,破坏了歌曲原意。
不过也能理解,选秀节目的歌曲,还得是为人服务嘛。 但是上周合作舞台的改词,再次把肉叔看愣了。 Jony J的《不用去猜》。 开头即迷惑rap: 我都是天亮了才睡,时间比Live(生命)还贵。

额,难道不是先好好活着,才有资格去谈时间成本? 再来: 曾经我为了去武装我自己,很快就学会了冷漠和妆发。

用妆发武装自己,肉叔梦回当年《素颜》四十五度的忧伤。 实际上,“妆发”的原词是“脏话”,而被“Live”替换掉的是“LV”。

应该有不少胖友反应过来,为什么要改这两处词。 它和开头的改编性质不一样,一个是主动创作,一个是自我阉割。 只要节目掏出剪刀,咱就别指望能看到歌词有沾染半点荤腥。
01
论改词,同档期播出的《青春有你2》和《创造营2020》还真能叫“神仙打架”。(之后简称《青2》和《创3》) 首先,搞颜色肯定不行。 《创3》一学员在采访中说到性感,字幕都要和谐成“成熟”。
更遑论歌词。 “进入身体”什么的违背无性繁殖理念,得改成青春纪念手册。 原:我可以,躲进你的身体,进入温暖的你。改:我可以,躲进你的心里,记录温暖的你。


听说《创3》有首歌叫《窒息》? 好咧,先把名字给你换了。 原:游走在若即若离的身体,想挣脱欲罢不能的窒息。改:游走在若即若离的回忆,想挣脱欲罢不能的沉溺。


港真,不改还好,一改就让人沉思,原本的“窒息”是否有SM的暗示。 至于更加露骨的一句词“我躲进梦里,曾和你翻云覆雨。”直接被删掉。 其实大可不必,很好改嘛,甚至能不动歌词原意—— “翻云覆雨”换成“鲤鱼打挺”,结合前面的“沉溺”,是不是有点上上下下,做爱做的事内味了。 再来。 现在是文明社会,不要喊打喊杀。 原:这年头膨胀,直接封杀你。改:这年头膨胀,直接fire你。

不要乱认辈分。 原:My son,多大吃点东西你还要喂。改:My song,多大吃点东西你还要喂。

不要封建迷信。 原:谁比谁好能差到多少,迟早都要向上帝报到。改:谁比谁好能差到多少,迟早都要向未来报到。

别问,问就是会带坏我们这些无性无欲、晕血晕刀、至真至纯的观众宝宝。 从以上的种种和谐、删改之中,想必大家已经掌握了部分改词的规律。 那么来无奖竞猜下,蔡依林的《play我呸》,将要改动哪些部分? 答案是几乎全改。 本意是表达社会乱象,改完后成了网游宣传语。 原:半夜一点的无邪浪荡睡衣姐妹,清晨五点的万人登山体操大会。改:半夜一点的大吉大利吃鸡派对,下午三点的万人出神蹦极排队。

尤其是这句,仅仅改了两个词,但一下子没了和后半句形成对比的反讽意味。 六零年代欧洲前卫地下/独立(原/改)导演讨论会,九零年代偶像复出签名握手拥抱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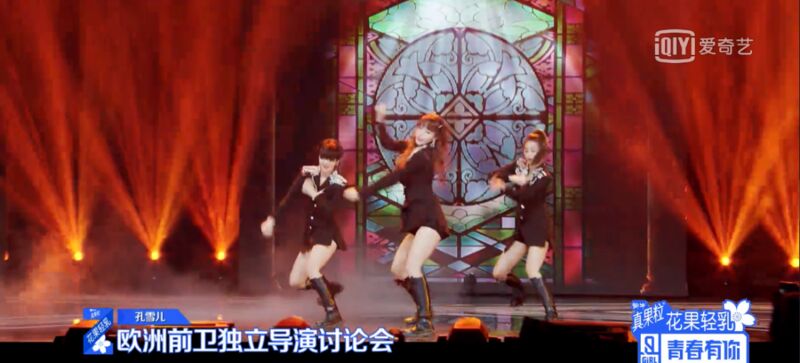
副歌部分更狠。 因为改的太多,肉叔做了张对比图,有点粗糙不要介意哈。

要知道,《play我呸》是先有词再有的曲,词正是这首歌的灵魂。 看似口水,但你细品,句句都是用后现代语境去表达社会现象。 关键词“play”和“呸”,谐音的背后是两种态度:不屑于当今的“装逼派对”,但既然置身其中,那就用玩笑乐观面对。 改完后呢? 不剩下任何复杂的思考,只有网上冲浪带来的简单快乐。 怪不得歌名也改成《play》,这可不是嘛。 而这把阉词的剪刀,又何止在选秀节目中停留。 任何有舞台、有歌声的地方,它都直达。 咔嚓一刀下去,管你玩诗情画意还是“月亮与六便士”,最终都指向统一的归宿—— 狗屁不通。
02
哪怕是线上演出形式的《相信未来》义演,也是要改滴。 而且改的地方让人摸不着头脑。 不能骂人是肯定的,但谁能想到骂自己也不行? 原:但是基于我那无耻的勇气……就像个冠军,无耻的冠军。改:但是基于我那无比的勇气……就像个冠军,无敌的冠军。
钢心乐队《冠军》 可以的,满满正能量。 再如,崇洋媚外也不行,哪怕只是提了一嘴,还是带贬义的。 原:不让你我之间注定是美国式的。改:不让你我之间注定是没过时的。

声音玩具《你的城市》 别误会字幕组,“没过时”三个字不比原来更能体现出爱情的相濡以沫,醒了很久还是很感动? 摇滚人啊,当时写词时有多不羁,现在改词就有多憋屈。 要是遇上用心点的字幕组,好歹还会照顾下逻辑。 郑钧写的《我是你免费的快乐》中“地狱”一词,被改成“定义”,马马虎虎吧。 原:粉碎我,我愿意为你下一百次地狱。改:粉碎我,我愿意为你下一百次定义。

遇上乱来的,如《我是唱作人》,摇滚人当场变成插秧者。 原:她是想陪你永生,还是想陪你下地狱。改:她是想陪你永生,还是想陪你下地,耶耶~

感觉后一句歌词是郑钧此刻的心声“这不合逻辑”。 要问郑钧为何能如此躺平接受,可能是因为有同期的Gai陪他。 同样惨遭身份转换: 原:江河湖海塞满了瞎子,上了公路全部遭压死。改:江河湖海塞满了虾子,上了公路全部遭压丝。

一个插秧,一个抓虾,果然,摇滚人和说唱歌手终会在《变形计》相遇。 不过,以上这些,和改词重灾区《歌手·当打之年》相比,都算不了什么。 《歌手·当打之年》,无差别覆盖所有暧昧词汇,以一己之力重新解构歌曲,打造出新世代华语乐坛。 徐佳莹《我还年轻 我还年轻》画风秒变恐怖片估计大家都知道。 原:给我一瓶酒,再给我一支烟。改:给我一瓶酒,再给我一只眼。
但其实第一期就有试水过: 原:你向我靠过来。改:你向我飘过来。
可能是因为反响还不错。所以持续贯彻了吧。 改词可以恐怖,原词却绝对不行。 华晨宇《斗牛》,“血管”改成“灵魂”,“尸首”谐音“失守”。 原曲的华丽诡谲荡然无存。 原:刺扎背部它血管爆破,激怒过后立刻凶暴如仇。改:刺扎背部它灵魂爆破,激怒过后立刻风暴如仇。
原:尸首气味中陶醉。改:失守气味中陶醉。
只要气质偏负面阴郁,就不能出现在台面上。 哪怕是歌名。 于是华晨宇的《疯人院》改头换面成《强迫症》。
这算不算一种对精神病人的变相歧视? 禁止不良嗜好,禁止心理阴暗。 它还要禁止真实。 旅行团乐队聚齐五人,全阵容上《歌手·当打之年》突围赛。 一首《Bye Bye》,去掉“bye bye”后就只剩下一半的词,几乎全有改动。 歌词直指这个“世界”被炒房热、潜规则、作秀、枪火等等包围,物欲横流、纸醉金迷。 所谓的真心、情怀都显得廉价。 改后的歌词忽略语句不顺,你甚至会觉得这个“世界”有点美好。 “浅瑰色的世界”很梦幻,“连结的精神坠毁”很团结。
它把所有深深浅浅的灰一并抹除,只留下茫茫的纯色画布。 单一、纯净,且虚伪。 可是歌词存在的意义,就不应该只有一种。 音乐是艺术,而歌词作为作者与听众间最直观的媒介,应该是承担着作者对这个世界的独特见解,是作者毫无保留地把七情六欲、心路历程撕裂给听众看。 尤其是好词,字字都经过斟酌,不仅讲究韵脚、对称,还要用最精炼的笔法,去传递最复杂的情绪。 怎么能随便改? 而且,华语歌的优势之一,不就是中文? 词库庞大,变换复杂,能给创作者足够的发挥空间。 都不用说原创,一个英中翻译都能翻出花来。 在不改原义的基础上,加工成诗经体:
波澜壮阔的英雄史诗,更凸显《viva la vida》激昂的曲风:
甚至单一的歌词,都能多样翻译,让感情层层递进:
你看,中文歌词的上限可以有那么高。 但是在剪刀的阉割下,连好好说话都困难。 本意支零破碎,修辞一地狼藉。 可惜。
03
难道歌手们都能接受自己的作品被这么胡乱修改?
怎么可能。
无法拒绝,那就用自己的方式反抗。
前段时间的芒果五四晚会,新裤子表演《你要跳舞吗》。 改词一般都是改成近义词或谐音,但新裤子把所有敏感词改成了反义。 “伤心”改成“开心”、“孤独”改成“热闹”、“冰冷无情”改成“浪漫多情”、“颓废”成“欢愉”。 原:每当浪潮来临的时候,你会不会也伤心。在拥挤孤独的房间里,我已经透不过气。改:每当浪潮来临的时候,你会不会也开心。在拥挤热闹的房间里,我已经透不过气。
原:在这冰冷无情的城市里,在摩登颓废的派对里。改:在这浪漫多情的城市里,在摩登欢愉的派对里。
背后是拖拉机,嘴里却唱着“摩登派对”,堪称当代反讽艺术家。 蹦迪歌都要讲究欢乐,那么涉及到同性恋的《盛夏光年》,得是禁曲了吧? 袁娅维硬是翻唱了这首,并且除了把“溃烂”改成“灿烂”,其他都没改。 节目组:你既然敢唱,那我就敢不打字幕。
在前后表演都有字幕的情况下,这种突兀反而欲盖弥彰。 然而,三年前的《歌手》,林忆莲同样翻唱了这首。 有字幕,且一字未改。
……节目组你变心得好快!
其实歌手再怎么在试探的边缘反复横跳,节目组定的界限始终在那里。
不会退让,更不会消失。
而且吊诡的是,这条界线也在反复游移。
换句话说,歌手能发挥的空间在不断变化。 典型案例如字字踩雷的《易燃易爆炸》。 16年,华晨宇上《天籁之战》翻唱这首时,尚还不用改动。
等到《歌手》,还是华晨宇唱,而“疯魔”、“下贱”、“杀人”等等字眼都已不能出现。
今年的《天赐的声音》,连“赤裸”、“销魂”等侵略性没那么强的词,都消失了。
原:还爱我赤裸不糜颓
下一个敏感词会是什么呢?不能逾越的界线到哪算停? 没人知道。只能明哲保身,摸着石头过河。 当然,不止是音乐圈,影视圈更是首当其冲。 今年重映的《美丽人生》,名台词“你想象不到,我多渴望和你做爱”被翻译成“你想象不到,我多渴望和你在一起”。
要知道这句台词是体现了主角性格的,正是这种出格才能让观众相信后来他在集中营的所作所为。 这一刀下去,切断了观众的视线,也破坏了作品的艺术性。 再者,界线不明的结果,就是自我阉割力度的不断加大,以致于矫枉过正,疑神疑鬼。 别说“性”,连“爱”都不能好好提。
《下一站是幸福》,菜敏敏和贺灿阳吻戏被删。
有人猜原因是他俩属师生恋。
可是,在大陆引进版《想见你》,主角的吻戏也被删除。
难道学生恋也是禁忌恋? 最魔幻的是。 “月经”这种再正常不过的生理词汇,何况还是用“那个”暗示。
左内地版,右台版
都被删除。 到底有什么好删的呢?
有什么好害怕的呢?
过度的自我阉割,只会让文艺大环境陷入恶性循环——
艺术需接受道德标尺的审判,歪斜一点就是三观不正。 人性的栖息之地不需要复杂,只能容纳得下非黑即白。 我们像是剥离欲望,一尘不染的机器,眼前是高度提纯的悬浮世界。 只是,没有灰尘,怎么反衬洁净? 没有肮脏,怎会渴望美好? 当所有杂质消失,只需要单一的意义。
那它将会变得没有意义。 肉叔想起岩井俊二的《燕尾蝶》。 元都是世界上最繁华的城市之一,高楼林立,拥有干净的街道和现代化的文明。 这吸引了几位外来者前来谋生。 而在功成名就之后,最让他们有归属感的,是一个叫“青空”的地方。 外来者飞鸿如此形容“青空”: 如果人最终的归宿是天堂,我想这里就是天堂了。
随着他的视线望去—— 那是片被垃圾填满的废墟。 却好像藏着无尽的生命力。
编辑:伊丽莎白的腿毛